辽河随想
作者 杨树槐
大辽河蜿蜒千里,若干支流由西、北、东三个方向汇聚于辽宁中部,然后一路向南,在距离渤海边大约30华里的地方,突然向东一个转弯,继而回头向西,形成了一个横写的U字型河道,从营口市西部注入大海。这就是美丽富饶的辽河湾,营口市则像一位苗条文静的少女,由西向东温柔地侧卧在大辽河的南岸。
从我第一次在营口见到大辽河,至今已整整60年时光。真是人生易老河难老。现在,我已年逾古稀,而辽河水依旧滔滔无期、年复一年地潮起潮落,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。60年来,我有时紧偎在辽河身边,和它共享欢乐与忧愁;有时又远去他乡,同大辽河难得一见。但是在我心里,大辽河就像我感情至深的亲人一样,从未被我忘记,许多有关大辽河的往事,时常在我心头涌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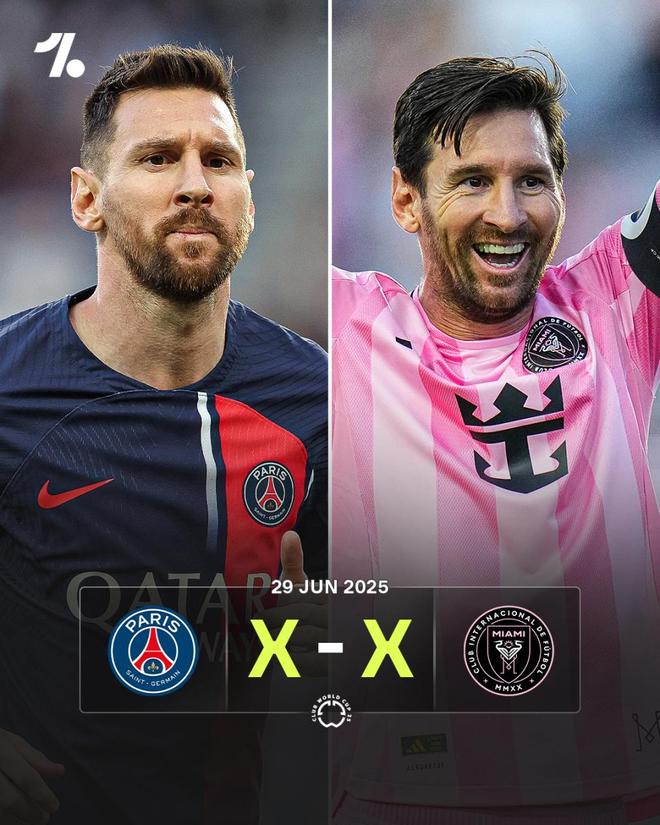
横渡辽河
1956年,我第一次见到大辽河。那年春天父亲因病去世。母亲为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长远生活考虑,于当年秋天,带着我们从几十公里外的渔村迁到了营口市。记得我们当时是坐着胶轮马车来到辽河北岸的。那里并没有城市的景象,只有沿河边的一条小街,街两边有几排低矮的民房。隔河望去,对岸的城市模样隐约可见。当时12岁的我只觉得这河面好宽呐!后来长大了,才知道大辽河涨潮时,渡口河面宽度可达千米左右。这么宽的河面,当时的渡船只有可容纳十几个人的小舢板。我坐在船边,看着船工吱吱呀呀地摇着大橹,船舷离水面还不到一尺高。我伸手划过清凉的河水,只觉得很有趣,却没有考虑到坐这种小船渡河是否安全。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,辽河渡口还没有大型渡轮,春夏秋三季,过往行人主要的摆渡工具,就是这种晃晃悠悠漂在水面上的小舢板,每人渡河一次,收费1角钱。如要渡汽车,则需将4条舢板并连起来,铺上木板,且一次也只能渡一台车。1957年以后,开始有了60马力轮渡,过河,比从前安全多了,也省时多了。到了70年代初,辽河渡口已经很具规模了。作为市交通局的一个下属单位,渡口建起了漂亮的二层楼,既有办公室,又有宽敞的营业厅。渡轮的吨位也大大增加,不但可以渡人,还可以渡车。每艘渡轮除了可渡几百名乘客以外,还可渡8台解放牌大卡车。码头也得到修缮和改建,汽车可以在河岸和渡轮之间开上开下。记得1972年我在营口市革委会宣传组工作时,还专门去采访过这个单位,报道过渡口的发展和职工们的事迹。
但是,面对宽宽的辽河,轮渡毕竟还是有许多不便。特别是在辽河封冻前和春天冰河即将开化这两段时间,既不能行船,又不能走冰,来往行人只能望河兴叹。许多营口人当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,如果能在辽河上修建一座大桥,那该有多好啊!但是老营口人都知道,在营口修辽河大桥绝非易事,因为这段河道近在辽河出海口,河面很宽,淤泥拥塞,对建筑的工程规模和技术要求极高,需要投入的资金在当时也是天文数字。所以,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营口人都认为,造这样的大桥只是个愿望,何时能建,只能说是遥遥无期。然而,时代的发展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,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,我们伟大祖国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,许多梦想和愿望都变成了现实。转眼之间,宏伟壮观的辽河大桥,像天边的彩虹一样横空出世,飞架于辽河口处,真如毛主席诗句中所说的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!据媒体报道,辽河大桥全长4.44公里,桥梁全长3.32公里,主桥长866米,宽33米,大桥中心最高处距河面约45米。2011年9月28日正式通车那天,我和夫人专门驾车从大桥上跑了一个来回,激动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我亲身经历了大辽河南北两岸,从舢板摆渡到渡轮往来,再到大桥横跨的发展过程,深深地感受到这正是伟大祖国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啊!
伴河而读
我的中学时代,续写了我同大辽河的情缘。我读书的营口市第四中学,紧靠辽河西部的河岸边,这是营口市当年十几所中学中绝无仅有的。学校的北边紧靠辽河,西边是同辽河直角相交的一条河岔子,当地人称其为西潮沟。据史料记载,学校校址原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海口检疫医院,始建于1919年秋,1920年7月竣工投入使用。该院以检查自海上进入辽河口的船只上的疫情为主要职责。院长是中国检疫、防疫事业的先驱、时任东北防疫总处处长的伍连德先生。到1956年营口市第四中学在此建校,距该医院开业已过去了36年。我在该校读了三年书,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辽河。课间和午间都会跑到辽河边去转一转、看一看。其间有两件与辽河相关的事情,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
一件是在辽河边砌炉炼铁。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,上级号召全民大炼钢铁,我们中学生也加入到炼铁大军之中。记得我们班有6个组,每组要建一个炼铁炉。我们组的炼铁炉是由我建议,建在了辽河与西潮沟交会处的一座水泥台上。这个水泥台宽有1米多,长有十几米,高有4、5米。西侧台下是西潮沟的淤泥和河水,北面是辽河,东南两侧同陆地平面连成一体。过去这个平台是做什么用的,我们不得而知,或许是船舶停靠的码头,又或许是对入港船只进行检疫的关卡,总之后来是废弃了。我们就在这个水泥平台上,用拣来的砖头石块砌了一座两米多高、像大地瓜炉似的炼铁炉。矿石和焦碳都是市里发下来的。我们按照技术人员教的程序,先是填进木柴,然后加入焦碳,最后添加铁矿石,一层一层地装进炉子,同学们在一片欢笑声中点火生炉。一连烧了几天,结果把炉子烧开了一道大裂缝。同学们最后把炉子扒开,取出了由凝固的铁水、焦碴和没烧透的矿石等熔在一起的一个大铁砣,这就是我们参与大炼钢铁的“战果”。不知这个铁砣是否已统计在当年全国钢铁生产的总产量之中了。多年之后再想起此事,使我深切体会到,如果我们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,基层就可能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做法。
另一件事是滑冰训练。当时学校时兴勤工俭学,各校一般都建有校办工厂。四中校领导用创收给学生买了统一的校服和一些教学用具。尤其令人兴奋的是,学校购置了足够两个班级使用的黑皮面高级冰鞋。我们小时候溜冰,都是在棉鞋上捆块木板,木板下面镶两根粗铁丝,就算是冰鞋了。现在一下子看到这么好的冰鞋,真是喜出望外。开始,体育老师带着同学们到结冻的辽河冰面上学习滑冰,后来因为辽河结冰时,冰块互相冲撞,常常此起彼伏地冻在一起,要找一块面积较大又平整光滑的冰面也并不容易,而且老师担心万一哪个地方冻得不结实,滑冰的同学会有危险,所以学校就在校区南广场上用土围成一个大圈子,里面注入半尺深的水,冰冻之后,成为我们上体育课时的滑冰场。可是,因为我从小就长了一双大脚,学校的冰鞋我很难找到一双合脚的,勉强穿着挤脚的冰鞋练了几回,但因实在挤得脚疼就不练了,所以至今我也没有学会滑冰,但中学阶段这些与辽河相关的往事,却留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没有忘记。

迷人景色
辽河景色,在我心中的确留下了独特的印象。大辽河是沿着营口市的北部边缘,从东向西注入渤海。隔河北望,对岸除了几排低矮的民房,就是一望无际的大片芦苇,这就是著名的辽滨苇场。南岸才是营口市区。所以,大辽河不像圣彼得堡市内的多条河流那样穿城而过,也没有巴黎的塞纳河、广州的珠江、天津的海河那样,两岸布满了宏伟的建筑,风光璀璨、富丽堂皇。但是,大辽河至今所保持着的原始质朴的美,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、令人难忘的魅力。其中深深烙印在我脑海,至今仍无限眷恋的,是大辽河夕阳西下的瑰丽风光。在我国,海岸线多数朝东,因此,站在海边看东方日出并非难事。但是,要想看夕阳西下落入海中的美景,机会就要少得多。而大辽河经营口市区这一段,正是由东向西注入渤海。本来,清晨时候向东看辽河日出也是可以的,但是在东部辽河湾处,已有许多高层建筑,所以看河上日出效果并不理想。然而顺河西望,看落日入海的美妙景色,却是营口人得天独厚的享受。当年,我常常在傍晚时分,坐在辽河岸边向西眺望,看着河水和海水连成一片,晚霞之上,一轮又圆又大的金红色太阳,一点点地向下移动。那日光和晚霞映照着河中涟漪,泛起点点金光。片片金鳞,闪闪烁烁,如同满河的金水,在缓缓地向西流动。半空中又时而有几只海鸥在滑翔。这种梦幻般的景象经常使我看得入迷,有时一坐就是一个小时,直到夕阳完全落入海平线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长大以后,我读了王勃的名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马上就联想到辽河夕照的景象,甚至觉得辽河的晚霞和夕阳之美,比王勃诗句所描写的还要真实生动很多。
近年来,营口市有关部门为了美化市民的生活环境,对辽河沿岸进行了几次维修改造,使渡口至成福里长达3.47公里的辽河南岸,变成了一条风光秀丽的景观带。坚固并造型美观的辽河护栏,如同蓝色长裙上一条鲜亮的花边,镶在辽河岸边。紧贴护栏是 6 米多宽的红褐色步行滨河路面,早晚在此跑步、散步、锻炼的男女老少接踵而过。滨河路南侧,约10余里长、百余米宽的开阔地带,是不许任何商业性开发的休闲区,十几块形态各异的绿地和公园,如美女的耳环一样镶挂在滨河路边。一年四季,都有市民在此休闲娱乐。许多老营口人,几乎每天都要来辽河边上走一走、看一看,看宽宽的河面上那滚滚西去的河水,看对岸一望无际的苇田,看前后不见首尾的护栏,看往来于河面的大小船只,看朝起于河东,晚落于河西的艳阳。他们和我一样,看了几十年的辽河,至今还没有看够。
我曾经羡慕芝加哥市区有一条百年不许商业性开发的沿湖景观带,回头看看营口的辽河景观带,觉得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绿色环保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,那么发达国家能够做到的,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。
本文选自《营口春秋》2017年第3期
发表评论
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